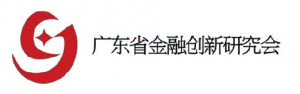【国际管理学会主席陈明哲教授: 管理的本质是要抓住人的本性】
日期:2013-12-30 作者:赵博 来源:文汇报
回首30年学术生涯,陈明哲坦言,“动态竞争”特别强调“行动-回应”的竞争本质,因为环境变化是常态的,企业需要积极的采取行动并做适当的回应,从挑战中发掘机会。而“文化双融”理论,主张跳出东方与西方、国际与本土、盈利与非盈利等看似非此即彼的概念,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中的有益部分,扬弃不足,从而实现管理的“双融”。
近日,第八届中国管理学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幕。能容纳千人的文治堂座无虚席,连后排走廊都站着听众。整个大厅灯火辉煌,聚光灯聚焦在主席台讲坛上,讲坛后却空无一人。国际管理学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教授陈明哲是当日的大会报告发言者,但他却并不愿意局限在三尺讲坛上,而更习惯穿梭在大厅的走廊中,他边走边讲,不时提问,然后将话筒递到听众嘴边,俨然像是现场采访。“现在我已经不会教书了,而是希望用一种交谈的方式与大家互动。”陈明哲说,希望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来启发思维。在这场题为《文化双融:一个海外学者的反思》的报告中,他似乎一直在提问。会议结束后,有人统计,他共问了60个问题,平均两分钟一个。
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30年学术生涯中,陈明哲一直追寻融合东方与西方管理学思想的答案。1976年,陈明哲毕业于台北大学。1988年,他在马里兰大学获得企业管理硕士与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近年来,他也先后应邀赴国家会计学院、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课,被誉为“全方位的整合型学者”。2012年,他被选为国际管理学会主席。
回首30年学术生涯,陈明哲坦言,自己在台东长大,家世普通、外无奥援,所有东西都只能自己想办法,“没有理论,就只能自己找理论”。正因如此,他开创了国际管理学界的“动态竞争”理论,这是过去20年从战略管理领域本身发展出来的三大理论之一,其中的“动态性”特别强调“行动-回应”的竞争本质,因为环境变化是常态的,企业需要积极的采取行动并做适当的回应,从挑战中发掘机会。根据“动态竞争”的本质,他又提出了“文化双融”理论,主张跳出东方与西方、国际与本土、盈利与非盈利等看似非此即彼的概念,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中的有益部分,扬弃不足,从而实现管理的“双融”。
动态竞争体现出中华文化中“人-我-合”的精神
文汇报:您是国际管理学界“动态竞争”理论发明人,能否介绍一下该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您是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套理论的?
陈明哲:这套理论其实源于理论和实务的差距。之所以会想到这套理论,一开始是受到了麦克·波特“五力模型”的启发。所谓“五力模型”,乃是以产业为焦点,提出影响产业竞争强度的五种力量。更明确地说,就是企业可以根据顾客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市场进入的难易度、同业的竞争方式(如价格、品质等),以及产品的可替代性,来判断某一产品是否具有研发价值。据此,波特提出了企业可采用的三类竞争策略:差异化、低成本和集中。就当时看来,波特的分析模型的确有助于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产业。
然而,当企业进入到某个产业时,波特的“五力模型”就难以见效了,它无法反映出供应链,甚至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也无法解释攻防交错的竞争状态,没能体现出竞争对手间“捉对厮杀”的动态性。因此,我认为这套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竞争,需要用一套更为务实的理论来解释企业与竞争者,甚至所有利益关系人之间的相对关系。
我认为,管理学者应该教会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怎样操作,因此我把理论浓缩为简单的几句话:竞争就是:一个行动,引发了一个或一连串的回应;即使没有回应,也是一种回应。直到后来,我意识到:原来在诸子百家中就有这样的“对偶”概念,无论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是《论语》中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都是从对方的角度反过来思考彼此的关系与下一步行动。动态竞争理论有两个核心概念:“动态性”与“相对性”。其中的“动态性”强调“行动-回应”的竞争本质,因为环境变化是常态的,企业需要积极地采取行动并做适当的回应,从挑战中发掘机会。“相对性”则主张企业需要逐一审视我和每一个竞争对手的相对关系,不可一视同仁。
动态竞争体现出中华文化中“人-我-合”的精神,强调竞争的主要目的是互利共赢,而非你死我活、你输我赢,赢者通吃。其中最佳的手段是师法儒家的“仁者无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子的“不争之争”、“无为而无不为”,而非以暴易暴。
坦率说,之所以想到创出这套理论,与我本人的背景密不可分。我从小在台东长大,没有显赫家世,没有奥援,一直是个边缘人,没有资源,所有东西都需要自己想办法。没有理论,就只能自己找理论,这条路就需要“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就需要你把所有知识拼凑整合起来。因此,我小时候的这一段背景,成了我最大的资源,帮助我从“没有”创造出“有”。
文汇报:动态竞争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竞争本身是动态的,即一个行动就一定会造成另一个反击。二是竞争本身是相对的,即我有优势,你也有优势,但我的优势需要跟你的优势比较,这样一来我的优势有可能会变成劣势,因此优势和劣势是相对的,而且即便有竞争优势也都是短暂的,因为对手会有所反应。这和中国古代五行相生相克是否有关联?
陈明哲:在哲学与文化层面,中国传统竞争策略观与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动态竞争理论的根源。西方强调,优势具有持续性特点,但在中国哲学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优势只是一时的,一定要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个有能力的企业要做到“以敌为师”,学习对手优势,并创造出自身的优势与价值,只有不停地与时俱进,否则就将被淘汰。这和中国人与时俱进、与时偕行的观念是相同的,也与中国人传统中的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相关。
不过,东方文化虽有很好的理念、哲学,却缺乏系统化知识和工具,因此,我的动态竞争理论也向西方科学借镜。西方的强项是社会科学的数据化,例如现在流行的大数据,我就采取了大样本的概念。作为管理学,要容纳出通则,而不是个例,因此需要进行大样本分析。而这恰恰是东方文化的短处,它缺乏科学证据来表述,就像武林高手论武功,更多的是感觉、境界,而非用数字说话。
文汇报:根据“动态竞争”的本质,您又提出“文化双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您提到:现代世界已经由“西方领导东方”转向“西方遇见东方”,新一代领导者必须能融合东西方文化,兼容合作与竞争,平衡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人际信任与法律关系、团队合作与个人成就。在一般人看来,“双融”之间有很多概念是相互矛盾的,如何才能化解这当中的矛盾,实现成效的最大化?
陈明哲:“双融”的本质是整合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东方与西方、国际与本土、盈利与非盈利、高科技和制造业等等。我认为:第一,我们应该有更宽阔的心胸来面对即使是对立的概念,跳出非此即彼的观念,得到“又此又彼”的概念。第二,我们要在两者之间挑选出好的部分,扬弃不好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又中又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觉得,管理的本质是要抓住人的本性。正如《中庸》提到的“率性之谓道”,无论东西方,人性的本质是一样的,你虽然吃辣,他虽然嗜咸,但我们若能抓到饮食的核心,基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世界大同的“同”,就是抓住了其中的“同”。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最大障碍是基本功不够
文汇报:西方管理学的“泰勒制”认为:企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泰勒在《科学管理》中写道:“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如今,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和电子行业中,泰勒制的观点仍很盛行,很多企业将员工的效率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一导致了很多负面效应,诸如员工情绪低沉,厌世情绪滋生等等。您认为,泰勒制的缺陷在哪里?
陈明哲:很多企业家推崇这种极致效率。当然,这当中有泰勒制的原因,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产业链上下游出现的挤压上游行业的结果。
几年前,我开设“王道薪传班”来培育全球华人企业家时,曾有人将“泰勒制”这种管理理念归为“霸道”代表,但在我看来,“王道”和“霸道”是相对的,不是说超越一个标准就是“王道”;低于这个标准就是“霸道”,或是在这件事上,你采取“王道”做法,在那件事上采取“霸道”做法。就我看来,一个真正的“王道”企业家应该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实行“王道”做法,让利分利。儒家所说的“内圣而外王”,其中的“王”字就是“旺”,把自己修好了,兴旺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现在,很多西方企业已经将“泰勒制”与人性管理做了很好融合。以“计件制”来说,虽然采用量化指标,但也同时把人性管理纳入考虑。从根本上说,还是应该实行“双融”,如果完全采用人性制,企业也很难管理,毕竟人性也有惰性的一面。
文汇报:目前,不少企业都提出了“人性化管理”口号。很多企业希望通过企业文化培育、管理文化模式的推进,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您认为,人性化管理是否是未来管理发展的趋势,其优缺点各是什么?
陈明哲:人性不是靠讲出来的,更多的时候是靠做出来的。好的企业其实没有口号,真的要执行是靠上面的人怎么做。言胜于行,当管理层一方面喊口号要压缩成本,另一方面却在奢侈浪费时,再响亮的口号都是空洞无力与苍白的。所谓的人性化管理,更多是要体现在点滴之中,例如不仅关心员工,也关心员工家人,这比谈人性化更有效。西方企业不太提人性化管理这种口号,而更习惯使用empowerment(授权)这种模式,期望能激发出人的力量和潜能。
文汇报:在管理学中,竞争与合作、公平与效率,似乎一直是一道两难抉择。既要保证效率,不吃“大锅饭”,又要实现公平原则,不让老实人吃亏;既要充分竞争,但有时有需要合作。您认为,这两组矛盾是否难以调和,是否存在非此即彼的局面?
陈明哲:其实,竞争与合作是一体的两面。竞争其实包括合作。竞争(competition)的原意是从拉丁文而来,其中的“com”是一起的意思,也就是朝一个共同目标努力,所以究其原始意义是包含合作的意思。我认为,竞争这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尽精确,“竞争”中的“争”并非争执、争吵、对立的争,而应该是“不争之争”。因此,竞争本身就包括了合作,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做事要留余地,而非你死我活。
在动态竞争理论中,竞争与合作是经营策略的主体。竞争是行动(攻击)与回应(反击)的交换与互动;合作是两家公司为达成互利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两者目的虽各有不同,却具有相依性,企业运作是动态的,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竞争者经常彼此合作,甚至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我把这种形态称作“竞合相依”,它是事业发展的常态。
效率和公平亦然,一方面要提高效率,但关键要有效能,结果要好。另一方面,创造利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利润的分配,这种分配一定要公平。有些电子企业之所以难以为继、举步维艰,是因为它取代了上、下游厂商,既想做软件,又想做硬件,与人争利,那就难以为继。
文汇报:您曾出任摩根斯坦利、杜邦等国外企业的战略咨询顾问。在您看来,外资企业希望在国内开展业务,最大的“水土不服”体现在哪些方面?同样,中国企业希望走出国门,面临的最大障碍又是什么?
陈明哲: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它们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大障碍,还是文化与执行层面上的落差。第一,在国家文化层面,很多外国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中国人特性的把握还不是很准确;第二,在执行层面,他们没有正视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始终相信,我既有的一套做法在中国照样能推行下去。其实,对外企而言,进入中国更需要“双融”,了解中国的国民特性。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黑不白,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就无法在中国市场立足。
同样,对于希望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基本功”不够。一些在国内取得成功的企业总指望在海外复制原有的做法。殊不知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有的是进入市场较早,有的是分享了政策红利。这些企业的确做大了,但不一定够强,要做强,他们还是需要回到“基本功”,要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方的主流。
在这方面,韩国企业做得不错。1989年,我曾经培训过34名三星的管理人员,他们结束在宾州大学沃顿的培训后,并没有打道回府,直接飞回首尔,而是被要求两个两个一组横跨美国大陆,从东岸到西岸,每一组沿途都必须经过15个州,深入了解美国的草根文化、百姓需求,回去才能报销差旅费。
美国商学院的模式过于急功近利
文汇报:您曾担任国际管理学会主席,也曾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在这20余年执教生涯中,您共培养出3000余名企业管理硕士(MBA)。而目前,这一课程在国内方兴未艾,很多高校也开设了MBA课程,也涌现出一批专业的商学院。您认为,美国商学院教育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其局限又在哪里?
陈明哲:众所周知,美国是商学院的发源地,商学院的整套模式是美国商业土壤孕育多年的产物,其主要目标是培养职业经理人。但在我个人看来,这20年间,美国商学院的“味道”变了。首先,美式学术教育深受西方绝对化的价值观影响,有着明确的排他性和程序性,几个顶尖商学院都习惯用数据、量化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对于其毕业生,美国商学院也非常看重其媒体的评量数据。这种教育导向使得大量美国职业经理人对人生成功的评判标准定格在年薪多少、身处社会何种阶层、占有多少的社会资源等等。有的美国人称其为“专业精神”,但这种精神忽略了东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人文内涵,演变成了过度功利。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的商学院也直接承袭美国模式,把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照抄过来。许多人的观念也被美式观念同化,将成功等量为年薪多少、在社会占有多少资源,将地位、权势、上流这些词汇挂在嘴边,将逐利视作经理人的本业,这种思维如果弥漫在整个社会,最终将形成人为的对立。冷静下来,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培训经理人究竟是为了在市场逐利,还是为了激发人性潜能?企业究竟只是冷冰冰的阶梯式架构组合体,还是应该包含人文关怀?创立企业,究竟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还是包含了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理想?
其实,还是应该把量化的流程思维返回到管理的“原点”。对企业而言,逐利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企业设置管理制度,究其根本还是激发人性与人的潜能,如果这些机制促使企业在实践中出现本末倒置现象,让人性让位于逐利,那么我就应该躬身自省,商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应该自我检讨。以前华人没有这方面基础,所以只能低头学习西方企业和商学院现有的机制、套路,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太多自己的“道”。在借鉴西方的同时,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拾华人自己的思想精华。
文汇报:随着中国的企业家队伍逐渐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日益加重。社会对于这部分群体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在学界,也有声音提出要为中国企业家“正名”。您之前曾提出观点:中国企业家是新兴的“士”阶层。您是基于何种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陈明哲:以前讲“士农工商”,商为末,由“士”这个阶层担当主体,而现在,更多的时候是由企业家在推进社会发展和传承,所以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快速崛起的企业家们,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新兴的“士”阶层。我认为,商人和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要做企业家,当然要有从商的观念,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商”本身意指“交易”,企业家则有创业的内涵,更着重企业的永续经营,而永续经营的前提是扛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而非交易。
任何企业其实都希望能实现永续经营,这包括家族企业。以前老话说:富不过三代,现代家族企业有更多机会能够富过三代,因为存活方式多了,一种方式是进入专业化的视角,进行专业经营;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股权或者公司治理,让家族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大家的步伐实质上是从“商人”往“企业家”在转型。
另一个需要转型的是所谓“儒商”的观念。尽管被冠以“儒”字,但儒商仍停留在“商人”的框架中,它固然有儒家道德的约束,并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但很难说是商业典范,所以算不上现代意义的企业家。我觉得,今后的传统儒商,包括冠以浙商、徽商、晋商的商人群体要从传统转变出来,逐渐形成成熟的企业家观念,以致于他们信奉、贯彻和执行的是一种制度、典范,而非一种文化习惯而已。在转变中,这个群体的一些优秀基因也应该被保留下来。例如:做事绝不能祸害乡里乡亲的信仰,这种朴素的“家天下”观念是成为现代新“士”阶层的一个重要原则,丝毫不亚于西方所强调的企业社会责任。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家扮演的角色是传承、推动价值观的传承。我希望企业家和学界融合起来,大家一起进步,逐步形成新的阶层,尽管这一阶层在西方被称作“中产阶级”,但在中国,我仍称他们为新的“士阶层”。